易立军论文精选
易立军论文精选
《离骚》题意申论
易立军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魅力的名篇。关于《离骚》的题旨,汉代已有歧义,后世纷争尤多,但要对“楚辞”进行研究,却又实在回避不了这一棘手的问题。
读《离骚》而求其真意,实非易事。清代王邦采在《离骚汇订》中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屈子之情生于文也。忽起忽伏,忽断忽续,屈子之文生于情焉。洋洋焉,洒洒焉,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别的姑且不论,“离”字在诗篇中多次出现,其含义似乎宽泛而又多变,这不仅使两千多年来难明其确训达诂,也使后人见仁见智,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解说。据周建忠先生统计,关于《离骚》题意有三十一类之多,① 近年还不断有新的观点问世,真可谓“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西汉刘安是研究楚辞的早期学者,《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亦云:“至于孝武帝,恢宏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淮南王对楚辞烂熟于心,必明《离骚》题旨。司马迁可以说是屈原的后世知音,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太史公深得《离骚》之神韵,异代同悲,百年同感,他对“离骚”的训解最值得我们关注。“离骚者,犹离忧也。”太史公似乎重点在解释“骚”字,而对于“离”字未置一词,因此从总体上说,题意仍不甚明朗。班固的《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王逸的《离骚经序》说:“离,别也;骚,愁也。”他们的共同之处对“骚”的理解一致,都说是“忧”、“愁”的意思,分歧在于“离”字。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对“离”字加以说明,会不会是“离”字字义普通,他以为时人能懂,就略而未谈了。值得注意的是,太史公在《屈原列传》里交代了《离骚》的创作背景和动机,这对我们探讨诗篇的题意很有帮助。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细绎《离骚》,字里行间浸润着去与留的烦恼,进与退的矛盾,守与变的冲突,欲弃置而又不忍的痛苦,诗人斥责群小当权,蒙蔽君王,对君王既不满又依恋,爱与恨相互交织,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这与太史公交代的“忧愁幽思”的创作背景与动机很相吻合,很可能是君臣产生隔阂初期的特有感情。姜亮夫先生说:“近三十年来,细绎屈子全部作品,定《离骚》之作创于怀王疏远之时。”② 汤炳正先生亦云:“《离骚》之作,是在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屈原遭谗被疏之后。”③ 屈原虽然“进不入以离尤兮”,但此时并未绝望,“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联系《屈原列传》,“离骚”之“离”似可理解为“隔阂”之意。这种观点可以从诗篇与古文献中找到许多证据,古人和近人亦有持此观点的,只是论证不够充分罢了。
《离骚》多危惧之词,充满忧患意识,如“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诸如此类,这是君臣有隙时期屈子心态的写照。在历代政治舞台上,君臣关系相当重要和敏感,由于君臣政见、志趣、爱好等不可能完全相合,加之中间又掺杂着左右君臣的势力,故君臣多间是不可避免的。屈原少年得志,王甚任之,“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未治”(《惜往日》),由于“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讎”,“疾君亲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惜诵》),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导致被君王疏远。屈原想寻找机会表白自己的心志,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寐”,“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事已至此,诗人进退两难,苦闷、焦虑时时煎熬着他,但屈子仍对怀王抱有幻想,企图将君臣关系重新修复。在《离骚》中,屈子营造了女嬃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太虚等一系列幻境,委婉而又曲折地流露出君臣产生隔阂时自己的满腔情愫。
《离骚》的“求女”喻义,自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未明诗篇题意所致。古典文学中以男女喻君臣司空见惯,《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典范。“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屈子既自比美人,也把君王比作美人,“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潘啸龙先生在阐述“求女”问题上独具卓识,他在朱熹“求贤君”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力主“求合于君”说,④ 笔者认为其说深中肯綮。其实,“求女”的答案可以从《离骚》题旨中去追寻。为什么屈子要“求合于君”呢?这是因为君臣曾相合,后来谗人间之才产生隔阂,诗人希望怀王能够回心转意,与自己“及前王之踵武”,离而复合,这是屈子在进退失据、美政无期情况下的善良愿望。
屈赋中“乱辞”具有“发理词旨,总撮其要”(王逸注)的作用,更是强烈地流露出“求合于君”的意念。“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清楚的知道,知我者唯有君王才有作用,没有怀王的器重,理想、抱负都会付之东流,存君兴国之志必将落空,美政更是遥遥无期,可“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诗中讲要从彭咸之所居,那只不过是一种不被君主所理解时的气头话,这似可看作是已被怀王疏远了的屈原唯一能向君王表白心迹的的方式。诗人责小人,怨怀王,叹时世,哀人生,反复申述其所忧所思,所虑所感,所怨所怒,而这一切都是以君臣关系产生隔阂为轴心而展开的。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这是屈子精神苦闷时的内心独白,屈子自道,最为可靠,“离”作“隔阂”之意讲,再明朗不过了。
“离”在古代文献中作“隔阂”理解,亦十分常见。《尚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孟子·离娄》:“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责不祥莫大焉。”屈原《惜诵》:“众骇遽以离心兮,又何以为此伴也?”《淮南子·本经训》:“天地之合和,阴阳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上下离心”与“君臣不和”连文类举,意思大体接近,这更可助证“离骚”之“离”为“隔阂”之意。
我们探讨“离骚”的含义,不仅要注重对《离骚》、《惜诵》、《惜往日》、《屈原列传》等作品的研究,而且要考虑到诗人与天文星象学有不解之缘。屈子的《离骚》弥漫着天上人间的迷离色彩,而《天问》如果不是出自精通天文星象的方家之手,无论如何也会令人难以置信。楚人向来有“天人合一”的传统,一九四二年长沙子弹库出土了一幅先秦时期的缯书(又称“楚帛书”)就是明证,该书中有两段共约九百字的文字,论述了天象与人间灾异的联系。⑤ 况且“离”在先秦时期确已作为星象术语使用了,《月令》云:“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据日本天文史学家新城新藏研究,《甘石星经》是中国星表的起源,甘氏和石氏的年代为战国中期,约公元前三百五、六十年前后。⑥ 《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甘氏说:“倚视离而复合,合复离为斗。”星象学知识代代相传,何谓“离”?隋以前仅存的星象学专著《灵台秘苑》卷一载有一些常用星象术语,其中对“离”的阐释具体而清晰:“离者,虽同宿共度,而南北乖隔,光不相及。”星体虽在同一宿,入宿度也相同,但一南一北,互不接触,星光也不交相辉映,这是隔阂之象。屈子具有诗人的气质,才情甚高,与楚王虽是初次相疏,由于没有心理准备,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想不通,承受不了。《孟子·万章》云:“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这话用来道屈子,实非诬妄之辞,“心沭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屈子在精神苦闷时借星象来寄寓自己的情感,亦应是情理在中的事。
一九八七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发掘,据简文考定,墓主名邵
力它,官左尹,葬于楚怀王十三年,系略早于屈原的同时代人,且身份高贵,与屈原曾官居左徒之秩位相近。包山楚简,共记录卜筮祭祷者,凡二十六简,其中一般祭祷祈福者四简,占疾病者十一简,占“事君”之吉凶者亦十一简。“事君”占卜是以“事王”是否“有咎”为贞问中心。除一般“尚无有咎”之外,又涉及“爵位”升迁的早迟,“志事”是否得申等,看来,占卜“事君”之吉凶,在楚国贵族大臣之间,或是一种颇为盛行的风尚。⑦ 难怪屈原与楚王产生隔阂时心烦意乱,去住不宁,从包山楚简这个独特的视角,亦可理解“离骚”即“隔阂而忧虑”之意。
戴震《屈原赋注》:“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⑧ 刘永济前辈认为,“其(戴震)说会通诸家,证以雅诂,最称周洽,今所当从”,并加按语,“今考定屈子作骚时,尚未远放江南,其后各篇,则在放于江南所作。戴氏‘遭谗放逐’如改为‘遭谗间阻’更为正确。”⑨ 王锡荣先生亦云:“按之《离骚》,诗人并不畏离别(‘余既不难夫离别兮’)而惧离心(‘何离心之可同兮’),故‘离骚’乃是忧楚王与诗人离心之意。”⑩ 戴震把“离”训为“隔”,于义为最允恰,笔者要强调的是,“离骚”之“离”是指感情上的隔阂,而不是地域上的阻隔或别离这一行为。愚以为,离,隔阂,不合,不和;骚,忧愁,忧虑,隔阂而忧愁,不和而忧虑,即为“离骚之本义。”《国语·楚语》伍举对楚灵王说:“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君王不行德义,那么近臣就担心与君王隔意见,君臣不和,从而危及近臣自身,远方的臣民就会拒命违令。楚怀王反复无常,不行德义,结果导致“路幽昧以险隘”。伍举之语被作为名言,书之当时楚国之史策,实即屈原命题所据。
“离骚”亦可理解成“骚离”,词序虽异,其旨实同,不和而忧虑,忧虑不和,意思基本一致。文学史进程表明,屈原是率先打破《诗经》以首句摘字命题的方式,根据诗篇内容创设题目的先驱,将“离骚”理解成隔阂而忧虑,篇题不仅是全篇之题眼,而且诗题与文章内容丝丝入扣。笔者认为,上述看法与司马迁的“离骚者,犹离忧也”的观点并不相悖,只不过深化了“离”的内涵,将其具体化罢了。
注释:
①周建忠:《楚辞研究热点透视》,《云梦学刊》,2000年第3期。
②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④ 潘啸龙:《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
《屈赋研究三辨》,《云梦学刊》,1996年第1期。
⑤ 皮道坚:《楚国艺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⑥ 新城新藏:《中国上古天文》,沈璿译,中华学艺社1936年版,第69页。
⑦ 汤炳正:《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
⑧ 戴震:《屈原赋注》,褚斌杰、吴贤哲标点,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1页。
⑨ 刘永济:《屈赋通笺 笺屈余义》,中华书局,2007版,第29页。
⑩ 王锡荣注《楚辞》,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998年一稿
2008年二稿
2013年端午节三稿
《天问》“启棘宾商"再探
易 立 军
《天问》素称难解,其中许多问题聚讼纷纭,向无定论,“启棘宾商”就是其中的一例。
王逸《章句》:“棘,陈也。宾,列也。《九辩》、《九歌》,启所作乐也。言启能修明禹业,陈列宫商之音,备其礼乐也。”洪兴祖《补注》:“《史记》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兴于唐虞大禹之际。此言宾商者,疑谓待商以宾客之礼。棘,急也,言急于宾商也。《九辩》、《九歌》,享宾之乐也。”朱熹《集注》:“窃疑棘当作梦,商当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误也。
盖其意本谓启梦上宾于天,而得帝乐以归。”朱子之说,因为臆度太过,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商],又为帝之误字。《天问》‘启棘宾商’,按当作帝,天也。” ①“商”为“帝”之误字说,普遍为学界所称道,但亦有持异议者,如楚辞学者游国恩前辈。游先生曾撰有《楚辞论文集》,论文集中对“启棘宾商”作了探讨,但没有作出明确的答案,谓“商者,或为帝之讹字,“或为高之误文”,“又或即以同音借为上,上亦天也。”②游先生在此问题上多说并存,意味着此问题仍有探讨的必要。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对“启棘宾商”亦作过探讨,仍未达成共识。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棘,急也,宾,朝见,启急急忙忙去朝见上帝,结果取来了《九辩》、《九歌》两种乐曲。上述说法于训诂有据,于文义却令人不安,至今为止,我们仍未找到相关的文献来支撑启急迫朝见天帝的观点。我国古代神话传说有启上天庭取得《九辩》、《九歌》一说,《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
郭注:“嫔,妇也,言献美女于天帝。”这与前引《天问》似乎相合。所以有人说“启棘宾商”就是“献美女于天帝”之意。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
《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宾、嫔古字通。棘与亟同。”盖谓启三度宾于天帝,而得九奏之乐也。故《归藏·郑母经》云:“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正谓此事。
“棘”通“亟”,《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匪棘其欲”,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棘”作“亟”,是其证。“亟”,屡次,多次之意。《国语·周语》“既毕,宾、飨、赠、饯如公侯伯之礼。”三国韦昭注云:“宾者,主人所以接宾,致餐饔之属也。”郭璞注《山海经》引《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宾”就是做客的意思,古者宾客至,必有物相赠,《山海经》经文说“开上三嫔于天”,这样才得到“《九辩》与《九歌》以下”。古事异闻,不必尽同,郭璞博学多识,必有所据。
《尚书·费誓》“我商赉汝”的“商”,《孔传》释为“商度”,清末研究金文的学者方濬益和刘心源指出,在殷周金文里,常常用“商”字来表示赏赐之“赏”,如刘氏就说:“商用为赏,古刻通例……不见雅训,惟《费誓》云‘我商赉汝’,仅存古文,后儒不识通假,乃以商度解之,非也。”《奇觚室吉金文述》l·27下)这是利用金文释读古书中后人不理解的通用字的一个例子③。下面补充几例。
殷墟卜辞有这样一片,即《前编》4·27·3:
辛巳卜贞,王其宁小臣缶,惠乍(作)册。
商(赏)□□,王弗悔④。
大意是说商王于辛巳命史臣(“作册”)加以安抚(“宁”)缶地的军队,并赏赐有功之臣小臣。
西周时期的《令簋》云:
隹王于伐楚白,在炎。佳九月既死霸
丁丑,乍册夨令尊宜于王姜,姜商令贝十
朋,臣十家、鬲百人⑤。
“商”、“赏”相通,这给我们重新释读“启棘宾商”带来契机。上古时期先民认为音乐来自神灵之赐,夏后启多次做客而受赏赐,得到《九辩》、《九歌》之乐,这与“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相吻合。《天问》“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孙诒让在《札迻》中说:“分地指启死太康失国之事。案竟与境同,此再申启德之不终,虽有生时瑞异,而身殁祸作,盖思忧则能达,荒乐则鲜终。《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不顾难以图后?’”⑥
姜亮夫先生曾指出:“就《天问》文例言,凡四句一韵,而第三句用‘何’字作问者,前后两句,必为正反两义,决无例外。”⑦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这两句是说启多次做客并受赏赐,带下来天乐,“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这两句讲启只图眼前逸乐,未能远谋,身死之后即罹祸。前两句说启得赏,后两句讲启受罚,这集中体现了“天命反侧,何佑何罚”的思想,还可进一步印证明“商”即为“赏”的观点。
《开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谓《九歌》。”又曰:“不得窃《九辩》与《九歌》以国于下。”义具见於《归藏》。⑧郭注《山海经》“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时说:“皆天帝乐名也,(开)[启]登天而窃以下用之也。"启多次于天庭做客,后来受赏赐,得到《九辩》、《九歌》,这是很自然的,但为何后人只说启从天上窃天乐,而不说受赏赐呢?可能是受“此曲只应天上有”的观念影响。按文艺起源的神话,人间的歌舞,最早来源于天界,是从天上得来的,而上天不会随便遂人心意才如此说吧。
以上说法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不当之处,恳予批评。
注释:
①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第905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② 游国恩:《楚辞论文集》,第154--155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
③转引自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6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李学勤《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第25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⑤刘启益:《西周纪年》,第12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⑥孙诒让:《札迻》,见《天问纂义》第210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⑦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第3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⑧郭璞注《山海经》,第171页,岳麓书社,1992年。
2006年一稿
2009年二稿
2014年三稿
“谣诼谓余以善淫”解
易 立 军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稀世奇才,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洁身自好,正道直行。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优秀人物,有人却对他有微词,说他私生活不检点,有作风问题。楚怀王身边的近臣对此说三道四,攻击、排挤屈原,屈原在《离骚》中自白:“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无风不起浪,屈原“善淫”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淫,邪也。言众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谮而毁之,谓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犹众臣嫉妒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唐代五臣注《文选》“离骚”篇时云:“谗邪之人,谓我善为淫乱。”清代钱澄之《屈诂》曰:“蛾眉见妒,情所必然,诬以善淫,无所置辩,谣诼二字,最巧最毒。”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女有淫行,虽美不足贵。”古人如此观照,今人承其遗绪。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前辈在《屈原赋今译》中如此说:“你周围的侍女嫉妒我的丰姿,造出谣言来说我是本来淫荡。”马茂元主编的《楚辞注释》:“善淫,这是小人们所谣诼的罪名。美貌的女子不一定就淫荡,但说美貌的女子淫荡,是容易使人相信的。”黄灵庚先生近年在《楚辞章句疏证》中说:“淫,邪也。屈子以蛾眉美女自喻,淫之为邪者,犹淫乱,中媾秽行也。”总之,“淫”是淫邪、淫乱、淫荡、淫秽之意。
“谣诼谓余以善淫”,说屈子生性淫荡,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有理有据,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说屈原与宫女或郑袖之流有染,尤其离谱。一是屈原洁身自爱,不会作出那样的苟且之事;二是说屈子与怀王争风吃醋,与君王不利,于己更不利。
《离骚》中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与屈原《惜往日》中的“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所表达的意思是相通的。楚怀王周围的群小是如何谣诼屈原“善淫”的,在相关的作品中是有迹可寻的。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由此可见,屈原之所以被怀王信任,是由于他有卓越的才能;而上官大夫与其争宠,心害其能,说屈原迷惑君王,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诸多迹象。《惜诵》云: 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也。专惟君而无他兮, 又众兆之所雠也。壹心而不豫兮,羌无可保也。疾亲君而无 他兮,有招祸之道也。
屈原在《惜往日》中,更是将所谓的“善淫”和盘托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
群小嫉妒怀王宠爱屈原,千方百计加以离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屈子心载秘密事,明法度之嫌疑,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怀王“虽过失犹弗治”,但心里到底还是不高兴,次数多了,就会加深对屈原的不满;而在政敌们看来,怀王被屈原牵着鼻子走,就是迷惑君主,“夺稿事件”只不过是导火线罢了。“善”,善于,擅长,在谗人眼里,屈原擅长迷惑君王,最会灌迷魂药。
扬雄《反离骚》:“知众娉之疾妒兮,何以扬累之蛾眉。”这也就是班孟坚、颜之推等人以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上官大夫之流说屈原迷惑君王,屈原说上官等人蒙蔽君主,双方名义上都以君王、社稷的利益为出发点,谁是谁非,怀王分辨不清。
亲小人,远贤臣,社稷就危殆。周厉王任用佞巧、善谀的荣公为卿士,《史记·晋世家》云:“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国语·晋语》:“将以骊姬之惑蛊君而诬国人,谗群公子而夺之利,使君迷乱,信而亡之。”
“淫”在古代汉语中有一个常见义项,就是迷惑的意思。《尚书·无逸》记周公告诫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要被舒适的享乐所迷惑,通俗地说,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逸周书·文传解》:“厚德广施,忠信爱人,君子之行。不为骄侈,不为靡泰,不淫于美。”《管子·任法》:“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者。”尹注:“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动于君,故君亦听之。”《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屈子千年蒙污名,只因“谣诼谓余以善淫”。根据上面的论述,“善淫”并非善于淫乱,朝中群小造谣中伤说屈子善于“迷惑”君王,这一观点,不仅有本证,且有旁证,理应传屈子心事。
“乱入池中看不见”解
易 立 军
盛唐诗人王昌龄,有“七绝圣手”之誉,他的《采莲曲》脍炙人口。《采莲曲》(之二):“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乱入池中看不见”中的“乱”,字面平常,字义却显得有点暧昧,一会儿被释作“纷乱”、“杂乱”、“混乱”、“狂乱”,一会儿又被讲成“慌乱”、“随意”、“争先恐后”、“眼花缭乱”。有些赏析者面对“乱”,保持沉默,一字不着,风流任人自赏,韵味得否,无从知道。总之,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涌心上。
刘学锴先生在《唐诗鉴赏辞典》中的阐释最具代表性:
第三句“乱入池中看不见”,紧承前两句而来。乱入,即杂入、混入之意。荷叶、罗裙,芙蓉、人面,本就恍若一体,难以分辨,只有在定睛细察时才勉强可辨;所以稍一错神,采莲少女又与绿荷红莲浑然为一,忽然不见踪影了。这一句所写的正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莫辨,是耶非耶的感觉,一种变幻莫测的惊奇与怅惘。这是通常所说“看花了眼”时常有的情形。
刘先生把诗中的“乱”理解成“混杂”,兼有“眼花缭乱”之意,立足点不同,阐释自会别具一格。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南朝《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王昌龄《采莲曲》的一、二句,显然是对莲池边采莲女子的描绘,“乱入池中看不见”,不是错觉,“看花了眼”的情形,而是采莲活动的真实写照。
“乱入池中看不见”如何理解,“乱”字是关键。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佳句,陶弘景《答谢中书书》谈山川之美,有“晓雾将歇,猿鸟乱鸣”的名言,唐诗宋词中对黄莺“乱啼”、“乱飞”有生动传神的描绘,绝对不是黄莺乱来一通。“乱”,金文字形象上下两手在整理架子上的丝线,它必然会呈现出两种情况:一种是将丝线理顺,有条不紊、错落有致,一种是杂乱无章、乱作一团。南朝萧纲《折杨柳》:“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杨柳乱成丝”,不就是贺知章笔下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吗?这是形容柳丝的错落有致。宋初陈尧佐《踏莎行》写燕子“乱入红楼,低飞绿岸”,“乱入”,形容错落有致地穿入,轻捷低掠,神态轻盈。“乱”字有一个久远的、约定俗成的义项,在南北朝到唐宋文人笔下频繁出现,就是错落有致的意思。
把王昌龄《采莲曲》中的“乱”释成错落有致,撰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并且切合情景。一群活泼的精灵,似出谷黄莺,衣袂飘飘,错落有致地飘入莲池中,一举手,一投足,技艺娴熟,神态优雅,且富有动感,这才是“七绝圣手”笔下采莲女形象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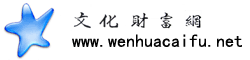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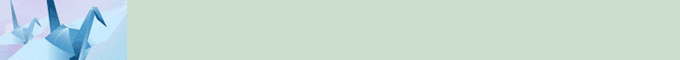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更多评论